|
从今天起,德金要开始主持这个专栏了。在这儿,咱不谈生活,不谈感情,不谈艺术,不谈社会,不谈苍生,咱只谈美食。为了一碗意大利面,军队都能放下屠刀,还有什么美食做不到的呢?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劳动人民,都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满足和快乐,还有什么比享受美食的权力更平等的呢?所以,每周五,在这,咱就放下立场,放下三观;抛开身份,抛开标签;忘了烦恼,忘了闷烦;清空肚子和头脑,脱掉布和皮,赤裸着、原初着,流着哈喇子,一起探索这个众生平等的桃源。为什么是周五呢?因为方便各位看官周末去吃啊!每期我会推荐一家餐厅和农大校内食堂的一道菜饭(毕竟咱是ICB读书小分队嘛,而且我推崇食堂,农大食堂这么好的资源不能浪费)。有时候我们也会推出专辑,为某一种美食,或是某一个与美食有关的事物立碑作传。 一家陌生的餐馆是一次美妙的偶遇; 一种全新的美食是一场动人的邂逅。 推荐餐馆: 北新桥卤煮老店 先来说说卤煮。卤煮是一种地道的北京吃食,出了北京,哪也没有。这道小吃是用猪肠、猪肺、豆腐在老汤里煮,比较地道的卤煮店还会加白肉。 专栏第一期,德金给大家推荐的这家餐厅是一家名噪京城的卤煮店——北新桥卤煮老店。高中时候,小肠陈是我的卤煮据点,我时常与哥们儿们一起到小肠陈吃卤煮、聊生活、谈理想、侃大山。现在我放假的时候也会约上这帮人去店里叙旧,重温当年时光。大学以后,常在一起的兄弟换了一批,我的据点也换成了北新桥。 这家店店面不算很大,还算干净、整洁。但对于卤煮这样一种走“下里巴人”路线的吃食来说,店面什么样并不重要。我仍然记得十多年前在鼓楼那边一个店里吃卤煮吃得满面红光、神采飞扬,而那只是个十多平米、满墙油渍的狭仄小店,但那天卤煮带给我味觉的冲击却是我至今依然念念不忘的。这也正是大多北京小吃的魅力,没有天花乱坠,没有十足噱头,外在质朴、实在,内在令人沉迷、流连。 走到点餐窗口前,“劳驾,一碗大肠卤煮,一瓶北冰洋”。交钱,拿条,给做卤煮的师傅。看师傅盛卤煮永远是一种享受。拿起一个大海碗往案子上一搁,先取一个火烧,刷刷点点切块,放入碗中。此时老汤香味已进入鼻腔,挑逗着你的嗅觉。再取豆腐、肺头,利落切块,放入碗中。取大肠,快刀一番,刀落肠断。最后拎起大锅中的一块浸满汤汁的白肉,片下一片,切长块,放入碗中,浇以老汤一勺,师傅就把碗递出来了。接过碗,明白的吃主儿还不能直接走人,要取腐乳汁、韭菜花、蒜泥淋入碗中,好辣者则再多取辣椒油。此刻,一碗完美的卤煮就在眼前了。 嘴和舌头忍不住大动,一一品尝,大肠肥腴软烂,不失筋道;肺头嫩滑香酥;豆腐不烂不老,不过分碎;火烧苍劲适中。地道。就着老汤的汁水,所有干货下肚,再一口汤,满头汗水淋漓,腹内温暖足实,神早已飞进了春宵。一餐真正的美食是可以吃到人精神高潮的。愉悦又有点恍惚,清醒又有点迷醉,这是最佳状态,也是这碗卤煮能够带给我的状态。 卤煮之外,也有精华。曾经这里是京城爷们儿、大妞儿的聚集地,不管白天晚上,在这吃碗卤煮,喝点儿小酒,酒酣而冽,人朴而实,聊聊那操蛋的生活,侃侃那神圣的大山。而今,这里也聚集着各地朋友,融汇着各种口音。人们在卤煮面前变得炽热、诚恳。破口大骂也好,满嘴火车也好,泪流满面也好,仰天长啸也好,这碗卤煮和对面的那个人都乐意承接着。在这个物质、精神爆炸的时代,在这个满嘴谎言的时代,在这个压力扑天盖地的时代,有如此安宁一隅,果然,生活不死,卤煮不死,美食不死,初心不死。 推荐菜品: 大肠卤煮、拍黄瓜、花生米、牛栏山二锅头、普通燕京啤酒、北冰洋汽水 其它卤煮餐厅推荐: 小肠陈(方庄店、天坛店、南横街店),晴源天地卤煮小吃店,陈记卤煮小肠,郭记卤煮,八条一号餐厅。 美食是腹中安稳,诗歌是心中安稳。 卤煮 善水德金大肠在孤独地游走,它挽起肺头的手,绝世的风流。也许你愿意吃豆腐,是的,豆腐谁都爱吃。碗底的火烧沉默,潜龙勿用。老汤陪着二锅头,唤醒了寂寞的舌头。它厌倦了政客的高谈阔论,室外的所有人都在高谈阔论。室内是个江湖,它找到了,生活。 有时候,我们追寻美食,追寻的是感官上的冲击和享受; 有时候,我们追寻的是封存在美食中的一段记忆、一份情感。 啊啊啊秋外热内冷人畜无害的五好青年小学那会儿住在石景山,家门口有个花鸟鱼市,市集边上有一家小店开在一个平房的二层,门脸儿不大,玻璃门上用红色不干胶贴纸贴着两个大字:卤煮。打眼瞧瞧其他地方,就再没有别的广告词了。这小店很接地气儿,通往二层的看似年久失修的铁架子楼梯总是“吱呀吱呀”地迎来送往,而店里那口大铁锅也总是经久不衰的冒着滚滚热乎乎的香味儿。 小时候没事总喜欢和小伙伴往那花鸟鱼市里跑,一来是家里养花养不活,常常需要添新;二来是打心里喜欢那些活物,总也看不够,常常是一出集市,天色也沉到一半了。小时候的我还没养成现在这个挑肥拣瘦的样子,皮实得很。肚皮瘪了更是禁不住那股子卤煮香味,虽然称不上打牙祭,但也兴奋得很。一进门儿就很敞亮,简单的几张桌椅板凳,已经坐了三四位食客,十几平方米的地界儿,又添了两三个小孩子就显得特别的热闹。记忆中是八块钱一碗,一份菜底一个烧饼,烧饼那时是一块钱一个。 “来咯!”已经记不清叔叔的面容,热情的招呼声却犹在耳畔。 我们站在大锅旁边伸手去接那白瓷碗,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回到座位上,瓷碗重,里面的料儿也给的实在。火烧切井字刀,豆腐切三角,小肠、肺头剁小块,浇之以老汤,佐之以蒜泥、辣椒油、豆腐乳、韭菜花。一碗热气腾腾的卤煮下肚,心里是说不出的快活。像多数北方美食一样,卤煮火烧以味儿厚见长,特别是戗面的火烧,因为吸饱了汤汁儿软而不塌,薄厚软硬都合适。肺头软嫩而咸鲜,豆腐亦是嚼得满口生香,不过我并不怎么钟情这些。要说最喜欢吃得部分,肠儿当之无愧。小肠是入味最重的,脆而不糯。有些吃不惯卤煮的朋友最不能接受的也是小肠儿,我只能替他们惋惜,味重才香的道理实是不可言传。 如今搬离了石景山,住进了学院路,戒辣戒下水,口味越来越轻,也真是很久没再尝过那口鲜香了,若要来一顿儿还得折腾一个多钟头的路程。如今提起笔来刻意回想起吃卤煮,赏花鸟的日子,竟忍不住暗骂一句:也许,小学那时候过得才叫日子。 青杏小一个兴趣广泛,热爱交友的北京姑娘前两天阅读小分队的群里时不时在聊卤煮,对我而言,卤煮不仅仅是一个小吃,它更是鼓楼姚记的缩影。我第一次在姚记炒肝是同两年没见的同学会面。因为转学去英国,同学说话时常夹杂单词,标志性的中音倒是一点没变,但是仿佛更沉稳了些,也洗去了两年前的稚气。我同她聊了很多,从同班时的各种趣事到她于伦敦的见闻。吃着老北京的传统小吃,耳边听着周围客人们的京腔,我的思绪却漂泊着。我仿佛看到了两年前我们在宿舍阳台推心置腹地交换心事,也仿佛看到了高一的冬天她穿五件衣服裹着熊逗得我们咯咯笑的样子。而现在坐在我面前的,依旧是她,不过是两年未见。我原本以为会存在时间与地域的隔阂,还担心要如何化解尴尬,真正见面的时候倒是完全没有了顾虑,像是天天相处的老朋友,相谈甚欢。 大学第一个寒假与高中室友团聚也是在鼓楼姚记,就是昨天,触动颇多。我同其中一个----我的闺蜜隔三差五约出来聊天,而四个人聚齐,实属不易。四个人多多少少有了变化,短发的留成了长发,直的烫了卷。但我眼里的她们依旧是在宿舍里穿着睡衣疯闹的单纯模样,三年以来发生的所有事,快乐与烦恼,理解和误会,好像都如白驹过隙般闪过我的脑海。我们翻出来过去的八卦,谁曾经暗恋过谁,谁又和谁暗中交往。小小惊讶之后反过来想想,高中,尤其是高三剑拔弩张的复习,的确会让我们有寻求依靠的想法吧。在大家默默吃着卤煮的时候,我看着面前的朋友们,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已经毕业了半年多,再过半年,大家会什么样子呢?“预计23岁会有一大波结婚的。”“哈哈然后27岁又会有一大波离婚的。”我们说笑着。真的不知道,时间这样神奇的物质会在我们身上施什么魔法。 我四下张望,后面的一桌是两个中年妇女,在交流教育方法:“我儿子说他物理总学不会……”她们点了丰盛的一桌菜,应该也像我们一样好久没见面了吧?他们旁边一桌是大人带着孩子,大概是五六岁的孩子,那时候的孩子说话特别可爱:“炒肝可难吃了!你怎么在吃炒肝啊?”饭馆里人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点餐的地方还在排队,刚到的人还在四处寻找座位。 我一瞬间觉得时间好像停滞了,自己好像变成了群像电影的镜头,记录着一个一个的故事。鼓楼的姚记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个旧故事的港口,载着过往的纷繁,我们在这梳理着过去,同时它又推动时间的船帆,将我们一同驶向了不确定的未来。 善水德金一只期待恋爱的单身狗,一个与你推心置腹的小伙伴了解我的人知道,我爱卤煮,我爱卤煮胜过爱任何一种外面餐厅里的食物。 作为一个北京老爷们儿,从很小的时候就和卤煮打了交道。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吃卤煮的了,但我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吃卤煮的那一天。应该是在我六岁那年,冬天。那时候,北京的天还很蓝,但那是个阴天——不是雾霾,是阴天。那会儿我周末会住在十里堡(朝阳区东南)。那天我跟着家人去吃饭,从十里堡坐着公交车到鼓楼——那时候的鼓楼还没有这么多兜售奇巧淫技的店铺。我不记得为什么没有开车,我只知道一路上我心情很低落,厌倦了这样长的一段路程,一心只想着回家。到了地方,不情愿地被家人领着进了一家小店,真真儿是小店,只有十多平米,四张桌子。依然不情愿地等着食物上桌,心想着这一切快点结束吧。但当那三碗卤煮被摆上了餐桌,被劝说着吃了第一口(没记错的话是豆腐,然后肠儿、肺头,我那会儿小,不爱吃)之后,就真的完全停不下来,直到桌上只剩了三个大空碗,脑袋上挂满了汗。太多的心理活动我真的记不起了,我只记得那第一口的感受,就两个字——爆香。 之后十年间或许又吃过屈指可数的几次卤煮,再后来,频繁地吃卤煮就是高中之后的事儿了。这时候的卤煮,之于我,不仅仅是美食,也是回忆、故事。多少次,在饭桌上,面前是一碗卤煮,脑海里,是那些年的一碗碗卤煮。 有一次高二带队参加完DI比赛(一个创新型艺术比赛),队员们起哄让我请客,也不知道说了什么,说着说着说到卤煮上了。一提卤煮,我立马来了精神,于是一行人来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家卤煮店。饭桌上几碗卤煮的蒸汽飘飘忽忽,北冰洋瓶子撞击的声音叮当作响,聊天声此起彼伏,不熟悉的队员之间加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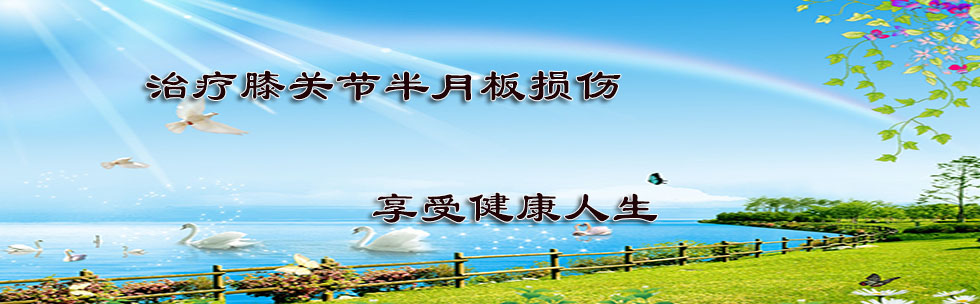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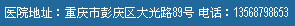 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